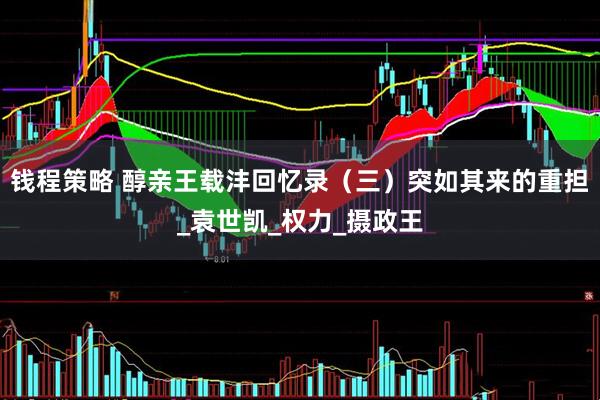
在光绪三十四年春初,我便听到内廷太监低声传言钱程策略,皇上身体健康每况愈下,瀛台的宫殿漏风,寒气逼人。二哥本身体弱多病,再加上心中诸多郁结,整个人也因此病体沉重,仿佛一只即将垂死的苍鹰,令人难以不担忧。看着他日渐虚弱,我不禁心中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,预感到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。
皇帝虽然在位三十多年,但始终未能传宗接代,若他突然去世,谁来继位?我对大清的未来充满了忧虑,因为这不仅是家族之事,关乎整个国家的安危。为了探知二哥的身体状况,我常常前往太医院询问太医们的意见,然而那些医者无计可施,甚至连宫外请来的名医也束手无策。无奈中,我看到太后频繁召集朝中大臣和宗室亲贵商讨继承之事。军机大臣世叙一向老实,他提议不如选择一位年长的皇族继位,以安定局势。然而太后听了这话显然不高兴,气氛紧张之下,世叙也不敢再言。他旁边的张之洞则提出,太后应该自行决定继承人,无需过多听信他人之言。因为张之洞在朝中的威望极高,太后对他也敬重有加,最后她还是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,决定让我的长子溥仪继位,同时过继给二哥,成为光绪帝的后嗣。我听到这个决定,心中百感交集,立刻进宫去谢绝。
展开剩余84%然而,太后的性格向来强硬,怎容我拒绝?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:“赶紧回去抱孩子来宫里。”我明白,如果再多言,恐怕局面会变得更加复杂,只得无奈地回到醇王府,告知母亲和福晋们这个消息。她们听后无不泪如雨下,难掩心中的痛楚。
我心中也是痛彻心扉,二哥的命运让我心惊肉跳,我真心不希望我的儿子也陷入这样的深渊。但面对太后的威压,我实在无法反抗。尽管家中长辈和福晋们埋怨我,我依旧无力改变这份命运。母亲更是痛苦喊道:“连我们的亲人都被抢走了,现在又要抢走我的孩子!”她泪流满面,情绪失控。我只能忍住不忍的痛,眼见朝廷的官差已在府外等候,只得将长子溥仪强行带走。此时,醇王府一片哀号,哭声不绝,甚至连前来办理公务的差人都感到难过。焦急之下,我找来了老大的奶妈,一同将溥仪送进了宫中。
不久后,太后的健康急转直下,这也许正是她为何如此仓促作出决策的原因。她之所以选择我的儿子,或许是看中了我的性格宽厚,认为我比较容易控制和依赖。尽管我心有不甘,但无奈于局势的压力,我只能顺从。太后最终赏赐我摄政王之位,我也因此成为了大清历史上第二位摄政王,权力远超六叔的议政王。但与此同时,太后为了制衡我,另选了她的侄女钱程策略,四哥的发妻隆裕作为太后,巧妙地牵制了我的权力。
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,不久之后,太后和二哥相继去世,大清的政权便由我一人承担。面对如此庞大的责任,我深感自己承载的重任过于沉重,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去应对。我开始着手改革,力图给国家带来一些改变,然而我的内心却并不确信自己能成功。
从一个普通的王爷晋升为摄政王,我心中总是无法忘记袁世凯给我带来的深深痛恨。是他害死了二哥,而现在掌握了政权,我决心要彻底清除这个人。面对袁世凯,我的想法很简单,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杀了他。但我也明白,这样一来,北洋新军肯定会暴动。所以,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,将他革职并赶回老家。虽然表面上看,这似乎是控制了局势,但实际上这相当于把虎放回山中,留下了巨大的隐患。这一决策的失误,也为日后清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。
我的集权方式与多尔衮相似,总是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,不容他人分权。为了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,我把亲弟弟载涛以及其他宗室如铁良、毓朗等人提拔到重要职位,试图通过亲情来强化自己的统治。但这些做法,也让立宪派的人不满。外部环境愈加紧张,国内的反清势力如同同盟会已在积极活动,列强也虎视眈眈。我却浑然不觉,依旧固守自己的政策,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挽救清朝的局面。
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,我决定借助家族力量,强化军权,设立海军大臣等职位,让家族的亲信牢牢把控权力。设立的咨议局模仿西方议会制,几乎把大清的权力交给了我和我的兄弟们。然而,这种做法却让立宪派的进步人士十分震惊。皇族内部的争斗愈发激烈,亲信之间的斗争不断,难以形成有效的政府。再加上内阁成员之间的分裂,如何能有效应对国家的危机呢?
然而,作为摄政王,我内心深知自己的执政能力并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。在皇族内阁的会议中,我几乎无法发表意见,只能默默旁观。回忆起溥仪登基的那天,太和殿冷气刺骨,小皇帝面对着严寒的环境,显得格外无助。我只能安慰他:“不急不急,很快就完了。”这句话,竟如同一根魔咒,笼罩在了晚清的头顶。果然,仅仅三年后,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,清朝的命运最终被定格。
我做摄政王的前三年,我怀揣着一线希望,想要有所作为。可到了第三年,我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,袁世凯也逐渐掌控了局势,而我却无法有效应对。在我的犹豫与无力中,大清最终走向灭亡。我的软弱和犹豫,最终让清朝的灭亡成为了不可逆转的事实。
慈禧太后当年处理袁世凯问题时的艰难抉择,最终也落到了我的肩上。她曾预言,若不及时解决袁世凯问题,大清必将灭亡,而我却未能采取果断措施,反而让这个问题恶化,纵容了袁世凯的崛起。
大清宣统三年,朝廷终于同意退位,而我站在退位的现场,内心却平静如水。回顾这些年,我深感自己并非天生为领导者,尤其是当家族的亲王们都站在对立面时,我越发感到自己处于无力的位置。那一天,回到家里,福晋看到我满脸的轻松,气得不行,告诉儿女们不要学习我这样的没出息。或许,她并未了解我内心的煎熬。
发布于:天津市睿迎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